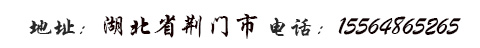邹振环西学东渐与明清中国的世界意识
|
晚明西人东来,被视为延续至今的“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早在年代,郭廷以所撰《近代中国史纲》即以16世纪的西人东来为起点,他在《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落后,“其症结并不全在近百年之内,实远伏于百年以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著名学者樊树志更是把16世纪作为“晚明大变局”的开始。15世纪末16世纪初,确实是世界大变局的开端,整个世界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社会文化开始重构全球化的路线、媒介技术、观念思维和审美标准。明清之际开始在中国渐渐形成的“世界意识”之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人的“世界意识”,其实只是“欧洲意识”;同样,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即“天下观念”。 晚明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知识界,就面临来自大航海时代欧洲有关世界地理新知识的挑战。本书着力描摹晚明至晚清知识人如何凭借既存的汉文地理文献,构建对于域外世界的想象。地理学文献较之其他异域情调的符号化产品,更具典型性和说服力。作为在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里,逞其幻思的思想动力,地理文献更易激发出多重多样的思想反应。从晚明至晚清,凡是有心追求地理新知的中国知识人,思考世变由来和因应之道,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知识环境中,通过想象和认识,探究着前所未知的寰宇情势和广袤无涯的地理知识。文献如人一般,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命,本书以具体个案的形式,阐释晚明至晚清的世界地理文献所承载的新知,如何在中国被生产和传播,从而为晚明至晚清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一个特殊的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方式。潘光哲创制了一种譬喻之说,认为近代中国知识人犹如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ofknowledge),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文献,各色地理信息、地理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殊方异兽、奇技妙器,或是令人“惊异不置”,或是令人叹为观止,或是令人掩卷深思,或是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观奇揽胜者的心怀意念,进而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resources)。 梁启超 明清构建的“知识仓库”中,最重要的是前代所缺的“万国之书”,梁启超甚至认为,理解中国与认识和想象世界是直接关联的。年他出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手订《学约十章》,其中第四章“读书”中称:“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年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再次强调:“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晚明以降有关世界的想象,使中国知识人通过研读汉文地理学“万国之书”,突破既存的知识囚笼,心驰域外、放眼寰宇,利用丰富的西方地理知识资源,形成了突破传统的巨大思想助力。 时空观念的认识,是人类思维活动最深层的依据。以纵向的视野来考察明清地理学汉文文献的演变史,我们可以发现多层次的明清西学东渐语境下汉文地理文献有一种不断叠加的层叠结构,表明了关于世界的想象和认识与明清地理学文献传播的互动关系。对历史纵向和横向的演变观察,需要探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展之轴中的联系及其因果关系。《庄子知北游》中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言天地大美,议四时明法,说万物成理是地理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故地理学家堪称“圣人”。天地大美不言,由地理学家诠释的众多地理学文献即可为天地立言。历史是空间上时间的延伸,想象域外空间是世界意识形成的基点,而认识世界亦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明清时期通过汉文地理文献认识所展现的“世界想象”,大致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传入中国的“西学”之空间想象有一个在域外和域内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地理知识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的不断叠加、逐渐清晰的过程。 先秦时代中国对东亚海域就有了不太清晰的认识,面对东海域外世界,齐人邹衍就有过“大九州”的想象。西汉张骞“凿空”,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始了关于中亚世界的想象。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僧的东来和玄奘、杜环等人的西行,《大唐西域记》和保留在杜佑《通典》中的部分《经行记》,为中国人了解印度佛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信息。宋元海道大通,阿拉伯商人的东来,带来了关于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想象。明朝郑和下西洋,给中国人了解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和东非带来了相对比较确凿的域外知识。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等,更是输入了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地理学的新知识。 从《西学凡》中最早传入的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和道科的“六科”,即现今所谓修辞学、哲学、医学、法学、修士学、神学,到中国学者徐光启按照利玛窦所传之学分为三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大者”显然是指神学、哲学,“小者”指物理学、机械学等,“象数”之学指数学。一直到晚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西学》则把西学分成天学、地学和人学三部分,其中地学以地舆为纲,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国人对西学含义的理解也渐渐在深化。晚清西方新教传教士传入大航海时代有关澳洲的新知识,在传入西方新地学知识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邝其照、薛福成等渐渐开始充当主角,他们提供的地理新文献,在新地学知识的介绍方面,更是改变了明末清初关于南极大陆的旧观念,提供了最新的关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和新认识。16至19世纪,中国开始漫长和艰难地从地域史走向世界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清地理文献为中国人提供了中西地理学交流的知识镜像,也为国人的世界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想象。 二、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对于世界的想象,往往联系着多样性的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而各种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又多是基于本土经验的想象。中国人在对世界想象的路径中,受汉文世界地图模型的影响最大。 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对于世界的想象,往往联系着多样性的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中,不仅介绍了欧洲的“五大洲”的观念,为中国人介绍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也介绍了各种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如《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所提供的珍禽异兽的异域动物的绘像,以及“世界七奇”展示的域外世界的奇异景象。在晚明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之前,中国人关于宇宙的观念主要就是盖天说和浑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两说都没有明确说明大地是一个球形,或谓天圆地方,或谓天圆地平。而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绘制开始,之后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和蒋友仁等,在中国构建了汉文世界地图绘制的系谱,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改变国人思维的知识点,如明确地球是一个球体,海洋是地球的一部分,整个地球有五大洲,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等。这一早期汉文世界地图的模型中,利玛窦和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还努力传送新世界的动物知识和七奇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一方面在汉文地图上沟通旧世界和新世界,另一方面也尝试在文化上沟通中西两种动物意象的互动对话 世界地理的认识和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地图模型方能建构,并依照地图模型的改变而不断改变。晚明至晚清这一汉文世界地图构建的系统,渐渐为中国地理学者和绘图者所接受,从《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到《万国大地全图》《大地全球一览之图》和《地球五大洲全图》,都先后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不同模型的汉文世界地图,形成了汉文世界地图表述的一个清晰脉络,展示了汉文世界地图观照异域世界的复杂过程。地图文献注重区域差异和空间表达,这种综合的空间思维的表述功能为我们理解日趋复杂的世界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这些汉文世界地图文献重构了晚清地理知识与国人理解空间的方式,任职于户部的官员恒廉称:“测绘舆图,西法实胜于中国,洋人无人不绘,无地不图”;同为户部官员的程利川更是进一步指出,不仅研究世界,即使研究中国,也需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yatea.com/xytjs/11052.html
- 上一篇文章: 钢铁项目开工高炉复工复产全面助力20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