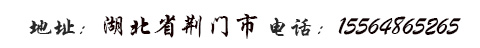汽车人李文波我和一汽大众偶然的
|
初期白癜风能治好吗 http://pf.39.net/bdfyy/zjft/160311/4785532.html 作者自序 我出生在南京,少小时随着大姐去了台湾。刚到时生活清寒困难,没钱上学,曾做过修理脚踏车的学徒,算是与“车”的初始接触,也开始对“车”有了兴趣。上大学时选择了“车辆系”,开始与车有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 六十年代的台湾,没有什么工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大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不到什么前景,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国留学。大部分人选择去美国,申请原子物理、化学、电机和核子工程等热门科系,因为只有这些科系才提供奖学金,毕业后也容易找到工作。 在当时美国大学里,根本找不到车辆系或发动机系。刚巧我有一位教授是留德的,他建议我去德国阿亨(Aachen)工业大学。阿亨工大既有车辆系,也有发动机系专业,何况德国的大学不收学费,学生在德国打工赚钱也很容易。 我被教授说动了,于是在年夏天揣着40美金,搭了一个月的船辗转来到德国的阿亨。为了生活我曾经做过泥水匠,搬运过石头,洗过碗,当过餐厅跑堂,擦过黑板,当过助教,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发动机的热爱,也终于获得阿亨工大的工程博士学位。 年我进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研究开发部,从事发动机的废气处理和新发动机的研究开发,也从普通的工程师晋升到部门经理。当时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狼堡(Wolfsburg)的总部有五六万员工,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担任部门领导职位的外国人。研发过程很艰辛,充满挑战性,我一直希望研发项目能在我手中成长并且开花结果。 但是事与愿违,从年4月15日第一位中国的部长访问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开始,我就被推到大众与中国合作的前沿。开始时充当翻译,因为我常提出自己的想法,后来变成顾问,而在大众和上海的谈判中,有时又会充担谈判双方的“和事佬”。这些都是“兼职”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研究开发部。没想到这双份工作一干就是6年,直到年10月,大众和上海的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签字为止。 一般情形,德国大众国际项目的合作伙伴都直接在工厂内。但我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德国大众的伙伴不仅是在上海和上海厂内,北京政府机构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因此在签字后我建议德国大众应该在北京设置办事处,以协调大众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时任德国大众董事长的哈恩博士听到我的建议后对我说:“在德国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工程师;但是既了解中国和德国,又了解大众汽车公司和汽车技术的工程师,只有你一位。中国项目对我们很重要,我希望你到北京做这工作。” 他的这一番话改变了我原来的人生规划。我接下这个任务,年开始了对我前途和命运有了大改变的全新挑战。 作者:李文波(原德国大众第一任驻京首席代表) 一 年,我到北京出任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驻中国第一任首席代表。 哈恩博士是对的,德国的确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他们用了30多年时间,把我们在70年代播下的种子培养成了今天全球领先的技术成果。 而我,虽然对不能回到自己钟爱的研究领域感到遗憾,却也从来没有对加入中国汽车产业对外开放合作事业而后悔。而且,正是由于我在发动机方面的知识,使我偶然发现和抓住了一款发动机带来的机遇,这款发动机在一汽选择克莱斯勒还是大众/奥迪作为合作伙伴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年年中,我交出在德国大众总部的工作来到中国出任大众汽车公司驻北京首席代表。9月底,吉林工业大学庆祝30周年校庆,吉林工大的陈礼藩教授邀请我去参加庆祝大会,让我喜出望外。 长春是吉林省省会,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看到东北两个字马上就联想到,50年代在台湾常常唱的那首抗日名歌《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再唱到:“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每每唱到这里,我的眼泪就会自然流下。 年,十来岁的我告别父母,随着姐姐离开南京到台湾。刚到时人地生疏,生活艰苦,常感到流离失所,也是在“流浪,流浪”,常常思念父母和家乡。怜人思己,与这首歌的共鸣之情油然而生。所以说,我对东北和松花江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没想到会有机会亲眼看到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当然我欣然答应了。 怀着兴奋的心情乘飞机从北京直飞长春。到达长春机场上空并没有看到遍野的大豆高粱,只见到类似年年底的北京老机场,跑道一旁停着几架军用战机,应该是米格15吧?整个机场上,我们是唯一的一架民用航空飞机。 等到飞机停稳后,一排穿着军装的士兵立正举手向我们敬礼,似乎是欢迎礼;返程我们飞机离开时,他们也一排肃立,举手敬礼,这是送行礼。整个机场看起来有点荒凉。 我第一次到达北京老机场时,是年年底,机场旁也是停着一排米格15,我搭乘的飞机也是唯一的一架民用航空公司飞机,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它是第一家能飞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航空公司。飞机停稳后,也有一排士兵立正敬礼。年北京机场早已没有这场景了,而长春还保留了这个仪式,而且延续了好几年。 长春飞机场的主楼既小又简陋,一条超短的行李输送带,几辆破旧的手推车,几个人就会把提取行李间占满。出了机场主楼门就是停车场,寥寥几辆吉普车和面包车在等着接人。马路上大部分是骡马车和人拉车,有时也会有辆大卡车,路面高低不平,满是坑坑洞洞。修车行和小吃店稀稀落落地散落在路的两旁,店面和马路面距离很宽敞,卡车就停在这里修理换轮胎,等同修车间。 吉林工大的牌楼很漂亮,门头上挂块红布条,写着“热烈庆祝吉林工大30周年校庆”。树很多,校舍很整齐。吉林工大前身是年9月为了配合一汽建厂和长期培养技术人才成立的“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年改名“吉林工业大学”。 30周年校庆庆祝仪式结束后,来宾分两组参观大学和第一汽车制造厂,我选择了后者。当时万万没想到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也改变了德国大众在中国的前景。 二 进入一汽厂区前,大马路的两旁分布着几十栋整整齐齐的标号住宅楼。厂区大门有块横石碑,是毛泽东题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大门后是一条大马路,应该是厂区的中轴线,两边整齐地排列着用红砖砌造的独立厂房和车间。 一汽汽车厂是年由苏联人设计并指导建造的,是中国第一座完整的汽车制造厂,年产仿斯大林4吨的中型卡车(Jis)3万辆,中国称“解放CA10”。CA10从年7月第一次出厂到年9月停产,总共生产了万辆。 年,一汽成功地仿制了克莱斯勒年款式的小轿车,命名红旗。年《人民日报》批评它耗油,翌年赵紫阳总理在北戴河的一句话,红旗就此停产了。 参观活动由原红旗轿车厂范恒光厂长主持,介绍了一汽的历史、现况和未来。最让我吃惊的是,一汽打算发展小轿车,而且已经具体地在进行。范厂长带我们从老厂区到新厂区,面对一片圈好的一望无垠的空地说:“这里有万平方米,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一平(平整土地)基本已经完成。它将作为年产30万辆轿车的生产基地。” 来长春之前我就已经了解一汽的历史和现状,毕竟耳闻不如一见,参观后真是觉得这里才是中国汽车生产的真正中心。当年政府把全国最优秀的专业人才都集中到长春来支持建设第一汽车厂。现在的领导班子,都是这批富有经验的精英。 这位范厂长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他的领导下,红旗轿车已不是年仿制年Chrysler的原样车了。据说当时一汽已初步具备了开发新车的能力了。后来一汽-大众在顺德的城市高尔夫项目也是他主持的。假如他们的计划真正实现了,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成功,上海大众在上海3万辆的前途,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为了节省投资,中国政府规定上海大众只能在老厂改造的基础上建厂生产,也就是说,老厂的框架不能改动,只能利用现成的支柱建新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上海的厂房是建在填积土地上,地基薄弱,无法承担大型的冲压机。德国工程师们只能在每隔一公尺内,打下三根32米长的钢筋水泥桩,一个车间就用了0根。厂房基建的费用和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预算,哪能跟在东北的地基上建新厂相比? 大多数上海配件厂是弄堂作坊,手工作业。车间厂房阴暗肮脏,只有走道上方挂着几盏超小的日光灯管,大部分的窗玻璃是破碎的,冷风直入。上海的冬天又冷又潮湿,车间内没有暖气,工人们不停地利用喝茶来取暖。既没产量,也没质量。怎能同一汽相比? 三 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不停地思考如何能和一汽合作?生产整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和上海合作了。除去整车,还有别的合作可能吗?生产配件! 再想一想,为什么不可能生产整车?上海大众生产的是中型车,依照德国大众的分级法,是属于B级车。那长春是不是可以生产A级的高尔夫家庭小车?长春新厂区规划年产30万辆小轿车,意味着只有A级车才有此销量。全世界没有多少厂家生产A级车,能同高尔夫相提并论的车型也不多。那是不是德国大众有希望呢? 我越想越激动。回到北京后就和吉林工大的陈礼藩教授联系,请他介绍我认识认识一汽的领导。而后,陈教授告诉我,有位一汽的厂长将到北京出差,我可以去拜访他,他就是韩玉麟厂长。 见面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韩厂长,并问他德国大众有没有同一汽合作的可能?至少在汽车配件的领域上可以找到共同的兴趣,这样既可以帮助上海大众国产化,又可以增加生产产量,减低生产成本。 韩厂长很随和,人很客气。他说一汽的项目才刚开始,等成熟后,有机会一定会再来找你。最后他很婉转地说你们是名花有主,而我们也相识恨晚了! 韩厂长告诉我,他是在北京等飞机去欧洲买发动机。我顺便告诉他,大众的西班牙厂也计划出卖一条发动机生产线。他听了,没做反应,我们就此告别了。当时我以为同一汽的因缘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还有很长的后续呢! 四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四位一汽的领导突然来到我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住所。其中两位我认识,一位是韩玉麟厂长,另一位是陆孝宽(一汽汽车研究所总工程师)。还有两位是黄兆銮(原一汽正厂长)和荣惠康(一汽规划处处长)。 陆总是我年在美国Detroit的SAE会议上认识的,当时我发表论文时他也在场。会后我们自我介绍,因而认识了,原来他在中国汽车界是鼎鼎有名的发动机专家。韩厂长则是一汽的有名技术专家,后来在一汽大众建厂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四位客人开门见山地提出,大众有没有可能同一汽合作?长春有没有生产奥迪的可能性?同时也邀请我到一汽访问。 年2月12日我应邀到长春,耿昭杰和韩玉麟两位厂长接待我,我们从桑塔纳的国产化谈到上海大众及一汽合作的可能性。 耿厂长特别提出,中国政府只批准了两家工厂生产小轿车,其一是上海大众,属于地方项目,另一家是长春一汽,是国家项目。 他又问我,上海大众是否打算继续生产奥迪?我告诉他,不会的。上海大众是老厂改造项目,德方人员一边改造旧厂,一边生产新车桑塔纳,目前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哪有精力再同时生产奥迪?而奥迪负责生产的董事HermannStübig曾到过上海,也不同意在上海桑塔纳厂内同时生产奥迪。 耿厂长还谈到,一汽的红旗已经停产,能不能把奥迪拿到长春由一汽生产?我答应去德国做做工作。但是长春30万辆的厂区,不可能只生产奥迪,我建议耿厂长引进大众的高尔夫。我们很坦诚地在各方面交换了意见,大家都觉得需要好好消化这次会谈的内容。 五 回到北京后,我首先把这信息告诉了上海的两位德方领导,希望他们到长春来看看。负责技术的HansJoachimPaul愿意走一趟,于是我陪着他去了长春。参观后,Paul很赞同我们与一汽合作的想法。 我们从长春飞回北京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飞机离开长春不久,机身突然下降,我们先以为快到北京了,后来才发现,飞机拉不上去一直在低飞,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山上的树林。 Paul问我有没有写遗嘱,我说没有,他说他也没有。当时他的脸色铁青,严肃地说他儿子还小,问我身上有没有纸好用来写遗嘱?我说,太晚了,即便写了也不会被找到的啊!我虽然说的很轻松,其实心中也在打鼓。 还好,飞机一直保持这个高度平安降落在北京机场。我向一位在机场调度室工作的朋友打听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正驾驶员腹泻,一路由副驾驶员操作,而副驾驶员是个生手。说真话,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开始腾飞,百业待举,到处都缺熟手。 上海大众的另一位德方副总经理MartinPosth,当时他是负责财务和采购的,应该是上海大众的第二把手,后来是负责大众集团的人事董事。 他坚决反对我的提议,也拒绝去长春参观。我在德国的顶头上司HeinzBauer和其他有关领导也都不赞成。 他们的共同看法是,德国大众在中国的第一个,只有3万辆的项目已经是麻烦不断,怎可能再加一个30万辆的新项目? 此时我得到的信息是一汽正在同美国的Chrysler谈判,长春打算引进生产Dodge。按照我的估计,假如他们成功,那对上海桑塔纳将会是莫大的打击。 这两个车型都是同一年代的产品:Dodge是年在美国投产的,标示83年车型;桑塔纳是年在德国出厂的,比Dodge还“老旧”一年。Dodge车长公分,轴长;而桑塔纳车长短了公分,轴长短了76公分。 用户对桑塔纳最大的批评就是后座不舒服,前座背和后座之间的空间太狭窄,后门也开不大,对后座人员而言,不只是坐得不舒服,而且上下车也很不方便。 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领导不开车,汽车都是由司机驾驶,领导坐后排,后座是上座,是领导的座位;在这点上,Dodge有优势。 再比较两车的其他状况,一为年产30万辆,一为3万辆;一为国产产品,一为合资产品,不管是生产成本或售价,Dodge一定低于桑塔纳。 一汽有完整的配套体系,自己有一百家以上的配套厂,产品是百分之百自制的;而上海的配套厂大多是在民房弄堂内,工坊手工作业。 一个是国营厂,一个是地方厂,在当时的中国,很容易看出来谁有优势。再说德国大众在德国和欧洲的配套厂家,看到上海大众只有3万辆规模,大部分都不愿意来中国投资,也不愿意技术合作。 一句话,“产量太小,没有兴趣”;假如年产量是30万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对德国大众很失望,也感到悲伤。而自己是有心无力,有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 六 年7月中旬,WaltherLeislerKiep来到北京,他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监事会成员,年曾来过北京,请我全程陪同。 他来华的目的,除去参观上海大众,也拜访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在他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上午去他落脚的建国饭店见面。他发现我看起来有点疲劳,就问我的身体状况。我很老实地告诉他一汽的事情,并且批评大众的态度。 他听后立刻打电话给上海的两位德方经理,证实了我的说法,并问我大众总裁哈恩博士知不知道这件事。我说不清楚,他立刻就说,应该让哈恩博士知道才对。还说哈恩博士正在意大利度假,刚刚装了一台传真机。 Kiep立刻写了几个字,让我试试发过去。内容大意是:请哈恩博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yatea.com/xytjg/10677.html
- 上一篇文章: 汽车人李文波我和一汽大众一切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