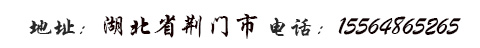张唐感悟景观的创造性
|
图1:杭州九里云松..张唐景观设计 讲艺术中的创造,不妨先回到艺术哲学发展的早期。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诗歌与绘画做比较,列举了它们之间的三条共性:都在仿效(imitate)自然;都有情节(plot)或者设计(design);都运用叙事功能(narrativedevice)。而这里的imitation,从词源学上讲是来自希腊语的mimesis,本意更接近representing而不是copying[VernonHydeMinor.ArtHistory’sHistory.SecondEdition.,Prentice-Hall,Inc.p]。一旦是representing,艺术的绝对性就成为疑问,生产者(worker/producer)在作品中是如何介入的?介入的动机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知识、训练、情绪、信仰)?其美学价值的来源是哪里?历史的或者文化的?作品的美学价值在哪里?Workersorviewers? 有了生产者的介入,作品不再是realtruth。“创造”这个词汇,含义模糊或者说多重(ambiguity),我倾向于它的语义学的一个层面,既是在讲生产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何把mind转介的过程。我们平常理解的视觉艺术的“创造”,就是要“看到”前所未有的“东西”;或者一种抬杠式的逻辑:别人往东我往西,大家上天我入地。(这种逆向思维固然算是创造的方法之一,但“也不乏是在一条路上的反复,”并没有摆脱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理解方式,肤浅的表达了生产者对作品的粗暴介入,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来源(origin)——历史的或者世俗的,以及生产者的态度(attitude)。如果不能摆脱这种思考方式,很难解释景观的艺术性的核心是创造,继而无法讨论景观设计可以创造什么,以及如何创造。 空间的创造性 景观空间不容易被认知(invisible),无论是对专业非专业人士。特别是我们长期以来使用picture,无论是效果图、照片、甚至动态的影像(video),一个二维图像做为主要交流及表达手段。很多照片上传达的景观项目,在现场感觉与照片非常不同——对于专业人士比较容易意识到的是“场地原来这么小”,“空间原来这么拥挤”;一些没那么“上镜”的项目,现场感受非常舒适——但是用相机怎么都拍不出来。 景观空间的训练,是我们十五年前在美国的景观学习中一门设计基础课。这门课程的设计获得过教学奖,并在北美几个大学景观系中普及过。后来在景观教育发展过程的各种博弈中被逐渐忽略,实践中也越来越少被提及。该课程的重要性之一是让学生建立了景观的3Dmind(也有研究认为3Dmind像色盲一样,很多人都没有),而电脑模型对此没有帮助。景观空间与建筑空间完全不同,首先它不完全建立在视觉(visual)范畴,还有身体(body)范畴,包括听、嗅、触等等知觉感受;其次它经常没有固态(objective)的边界,随着人的动态变化而改变。类似的见解,可以在很多理论中读到(比如BernardLassus,ElizabethMayer等),也可以通过长期的实践体会。这里通过张唐的几个项目略做解释。 杭州九里云松的空间结构,是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最费心思的部分。虽然项目照片上呈现的是屏风式墙体、山水画式的水景墙体等“看得见”的“东西”。这个不到7千平方的小项目,空间被建筑固定。如果翻看原始地形和现状,你会发现主体空间的单一和“顽固”。我们无法改变其大小、边界(三条边界由建筑固定,一条是外部道路)、甚至体量(volume)——在一定的视域范围内,vertical永远主宰(dominant)horizontal(或许这也是景观被建筑主宰的宿命)。改造后的空间,是尺度和身体感受上的——中间水面上的一条汀步将“顽固”的单一空间暗示为二,一边是水景,对面是保留现状大树的草坪。水景以窄沟的形式在草坪周边围绕得以完整。大量的草图研究后直到找到了这个关系,感觉如获重释,虽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好在大部分人“看不到”也不追究,直到去年在被教授StanislausFung的采访中被问起为什么。 如果用“阴阳”解释这个“一分为二”是一种cliche,不妨试一下德里达(Derrida)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核心Binaryopposition:ideology的概念里往往暗示了hierarchies,常常把思想、态度、物体等概括成pairings——这个/那个(either/or),光明/黑暗(light/dark),真理/谬误(truth/falsehood),秩序/混乱(cosmos/chaos),理智/不合理(rational/irrational),科学/迷信(science/superstition),男人/女人(man/woman)...德里达用男人和女人接着解释: 男人的对立面(女人),实际上拥有庞大的力量决定他/男人的特性(identity)与命运(destiny),因为要证明他是谁(whatheis),就必须知道他不是谁(whatheisnot)。从这一点上看,女人对男人就有威胁(threatening),男人应该排斥她,取缔她,但是他不能。因为否定女人就是否定男人自己[VernonHydeMinor.ArtHistory’sHistory.SecondEdition.,Prentice-Hall,Inc.p-]。 对于中国的阴阳哲学,我有类似的理解:黑与白之间不是一种对立,而是互相依赖的共存。没有黑的存在,白不能成立;反之亦然。学者S.Fung对此使用的propensity(势),非常精准的说明了这种二元对立之间的张力(tensionofforces)[StanislausFung,MutualityandtheCulturesofLandscapeArchitecture.P]。这种“势”的存在,除了围棋中的“掌控”以外,还包含了主次、平衡。我们在九里云松的主庭院中找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决定部分取决于空间的周边情况(objective),部分是我们的取舍——轻重、主次、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行业中的绝对经验主义。理论可以做“马后炮”式的解释或者交流,但不是设计时的根据。坦白的讲,无论理论多么发人深思,都无法成为教条指导我们如何具体做设计。 与九里相反的一个案例是杭州西溪木守酒店。项目一开始和建筑师达成的共识是保持现场原有的景观结构:水塘,坝体,小径,林地......所有的功能性场地是根据现有条件磨合出来,费的是另一番脑筋。这时的挑战是,如果功能上需要一片林地是停车场,怎么保住原有场地气质又有停车功能?如果塘边需要一片功能草坪,怎么处理湿地与草坪的边界和衔接?根据现场条件决定的功能空间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塘是否需要视觉中心,如果需要位置应该在哪里?堤坝上是否需要视线引导,强化边界还是打开?界定的空间与原有的自然状态怎样过渡?用墙体截断还是自然汀步引导?...现状以另一种方式限制空间的变化,同样挑战我们的创造力。 不过我个人觉得,过度的沉浸于现场,对空间的想象力是不利的。或者说这是现代景观设计师和builder,以及早期造园者的区别。对现场的空间感受需要保持第一眼时瞬间的印象,以及脱离局部片段式的场景(discreteintervals)从而对全局的把握。 材料的创造性 景观材料的创造性,极大的受限于户外这个条件。户外还意味着地域差异性。风、雨、日照、潮湿等气候条件让景观材料的突破比较缓慢:有的材料被创意的应用,但可能局限在室内;有的北欧的景观意向图片非常“酷”,但是我们的场地可能在中国南方潮湿、植物繁盛、缺乏视域的山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条件和环境背景。 (景观)材料的突破还依赖于当地(国家的、地区的)的技术。比如张唐目前在构架上比较局限于钢材,因为无论在质量、工艺还是价格上,中国的钢材较之木材、竹木、塑料在户外的表现都相对最有保证。做为设计的被委托方,我们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保证设计的最终效果、可行性、耐久性,对任何创意和突破在适合的条件下、使用者的诉求下比较慎重的提出。 材料的创造还需要考虑景观空间尺度,从宏观讲是景观的boldness,从微观讲有roughness。我觉得这是景观材料突破和挑战的难点,不仅是地域、户外的合适与否,还有对它的尺度感、粗糙程度的考量。过于细腻(delicate)的材料,比如玻璃,其肌理、质感、整齐度,使用时就需要考虑与场景的契合。 设计师都会抱怨自己的设计受限。我们的确经常苦恼并挣扎于各种限制条件:地库、覆土、通风井、绿化率、商业开口、销售需求.....说实话,中国的景观项目远比美国的复杂得多。但是同时又不得不说,这些限制条件和设计师的创造力没什么关系,并不是说在一块场地里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花多少钱花多少,想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就可以做出最好的创造了。相反,很多非常有创意的设计,都是被各种不得已逼出来的。创造力的训练往往是基于最严苟的限制条件。建筑师及教育家KynaLeski在她的书“TheStormofCreativity”中讲了一门她教授的建筑入门基础课。她只给了学生一种材料,她称之为“一种固执的、天性倔强的材料”(astubbornortemperamentalmaterial),因为她知道这种材料“不会听令于任何‘指示’”(wouldnotrespondtoanythingimposedonit),相反,学生需要“聆听并回应这种材料”(listenandrespondtothematerial)[KynaLeski.“TheStormofCreativity”..TheMITPress.P17]。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需要聆听和理解,材料、场地、别的人。真正的创造,不会因为任何条件受限。 对材料的创新还往往导向对构造,以及向传统工艺的挑战。我曾经在Umass的景观理论课上学习了瑞士的桥梁设计师RobertMaillart。与liberalart院校的抽象理论不同,教授JosephSRV.把理论研究建立在系统的艺术、建筑、结构等广泛的方位和视角的实证案例上。和他的景观基础课一样的严格繁重,我们需要写4篇单项论文和1篇综合论文,我被指派的几篇分别是Shakers,RobertMaillart,LuisBarragan等等。Maillart的桥梁,可以说是用混凝土代替钢铁的创造性的开端。挑战轻、薄的桥体是基于三个原则:最少的材料,最经济,最大程度的美学表达(minimummaterials,minimumcost,maximumaestheticexpression。)他的镂空箱体(hollowboxgirder)和三铰链(three-hingedarch)的结构在瑞士的TheSalginatobelBridge中达到巅峰。设计师把不需要受力的拱体部分简化成箱体结构,使用三铰链的目的之一是使得结构在山体轻微移动时可以有调节能力,在选择与山体连接位置时考虑施工过程脚手架(scaffold)的用量最少。 图6:TheSalginatobelBridge,Switzerland,,byRobertMaillart. “盘曲在两山之间...游弋在空中,忽左忽右...这个在瑞士SimplonPass的构筑物,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JohnMcPhee,我最喜欢的美国当代non-fiction作家之一,在他年初纽约客(TheNewYorker)上的文章中这样描写TheGanterBridge。桥的设计师,ChristianMenn是一位世界上另一位无可比拟的瑞士桥梁设计师、结构工程师[JohnMcPhee,TabulaRasa,TheNewYorker,January13,Issue.]。Menn早期的作品,受到Maillart的极大影响,但同时为了节约持续快速增长的人力成本,他把竖向的箱体结构支撑间距拉大,同时对预应力(prestressing)的运用保证了拱形支撑的牢固度(deck-stiffenedarches),比如TheReichenauBridge。后来,Menn的桥梁逐渐形成个人特点,比如大跨度、小断面、集中受力等。这种方式使现场的脚手架设计简单易行,比如TheFelsenauBridge,从柱子的两头分别悬挑施工,使它不仅可以跨越山谷,还可以保留现状的居民和住房。 图8:TheReichenauBridge,Reichenau,Switzerland,,byChristianMenn. 图9:TheFelsenauBridge,Bern,Switzerland,,byChristianMenn. 图10:TheGanterBridge,ontheSimplonRoad,Switzerland,,byChristianMenn. C.Menn于年去世。他生前的“老年计划”(old-manproject)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本土之间,设计一座核心跨度为世界上最长的2英里的悬索桥(Cable-stayedsuspensionbridge。)“而我的老年计划是,写一部关于印第安纳农场的25,头牛。”McPhee写道。从他六十年代第一本书“桔子”(Orange,)到后来俄罗斯六-七十年代地下艺术的救赎(TheRansomofRussianArt),怀俄明州的地质(TheRiseofPlain),在船上的海洋生活(LookingforaShip),写作和发表的DraftNo.4......这位今年88岁的作家对美国文学界中nonfiction文体有开创性的贡献——对习以为常的事件不厌其烦的追根问底、没有尽头的细节、纪实文学中的故事性、幽默的观察及不去judge的观点.......印第安纳农场的25,头牛,只是想一想,就已经开始让人微笑。 “直觉”与“创造” K.Leski在她的书“TheStormofCreativity”中还阐述了Sensibility与Creativity的关系。她打了个比方我觉得非常有同感,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用钥匙去开锁,锁有些卡。于是就不停的试,直到有一个瞬间感觉到里面轻轻的、可动的那个铁片。这个瞬间就是:感觉到了一些,不是特别知道感觉怎么样,也不知道感觉的是不是真的要发生,并且怀疑自己的感觉(feelingsomething,notquiteknowinghowIhadfeltit,notknowingwhetherwhatIfelthadreallyhappened,anddoubtingmyownperception)。直觉不只是你如何通过感官获得信息,还是你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形成链接自身和世界的概念,它是创造过程的一项元素(Itisanelementofthecreativeprocess)[KynaLeski.“TheStormofCreativity”..TheMITPress.P83]。 结构艺术的发展,有一个辉煌时期是18/19世纪的欧洲。伴随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politicalrevolution,法国对英国自认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感到不适(defeated,depressed,anddishonored,)从而产生强烈的愿望重获往日光辉(recaptureitspastglory)。GustaveEiffel在此时期成为structureart的代表人物。他总结结构艺术的三个原则:大尺度,极度有限的使用功能,体现社会价值和美学观念(largescale,narrowlydefineduse,theembodimentofsocialvaluesandaestheticideas。)后来柯布对他的评价是“不仅是美的创造者,他对比例有着让人钦佩的直觉,他的计算受教于此,他的目标是优雅(Hiscalculationswerealwaysinspiredbyanadmirableinstinctforproportion,hisgoalwaselegance.)”[DavidP.Billington.TheTowerandTheBridge-TheNewArtofStructuralEngineering,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64]。 就像Kyna描述的,直觉是一种敏感度。这种敏感度会影响创造力。或者说直觉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天马行空不同,他/她需要把这里挪一挪,那里偏一偏,寻找打开锁的那“咔”的一瞬间。缺乏这种敏感度,看不出来哪里好或者不好,亦或无法安静下来左右的尝试,这把锁终将很难打开。 那么这个“直觉”到底是什么?是“灵机一动”么?来源于哪儿?我想或许英文中的subconsciousness,潜意识,比instinct更准确。创造不是“无中生有,”那它又是什么呢?HenriPoincare,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把这种思考解释为unconsciousness,无意识,一种“既非佛洛依德式(Freudian)被压抑的恐惧和欲望,也非不用动脑筋的开车或者不用思考怎么说的句法,”而是“大量的潜伏的复杂问题的孵化”(theincubationofhugely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yatea.com/xytcx/10833.html
- 上一篇文章: 布雷西亚联赛九轮不胜恐难有作为,那不勒斯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