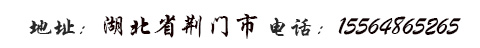解读査道炯南南合作运动历程对一带一
|
北京看白癜风 https://jbk.familydoctor.com.cn/bjbdfyy_tsyl/ “ 南南合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反殖民、反霸权的第三世界政治外交大团结基础上试图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斗争运动,转变为21世纪发展中(南方)国家与发达(北方)国家之间、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殊途同归(谋求南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新世纪南南合作的共通性诉求,不再是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广泛的大团结,而是接受了多个国家、多重力量竞相影响发展进程的现实;不再是革命与相互排斥,而是开放性探索。围绕发展道路的摸索,也不再集中局限于从富国或强国发出的单向引导。本文通过回溯南南合作的历史轨迹,并试图从中找到经验教训,为更好地谋划今后的“一带一路”事业,提供参考性思路。 本文首发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上)》,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 ” 前言 作为联合国系统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南南合作办公室”(UnitedNationsOfficeforSouth-SouthCooperation)于年开始运作。这意味着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从轰轰烈烈快速走向被人遗忘的南南合作运动在联合国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得到了重新确认。毕竟,众多的国际合作倡议或协议、条约,是否建立起了常设性执行机构,其后续效应是大不相同的。联合国常设机构的变化,从名称到实际功能,都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而得出的最大公约数,部分因为机构运行的预算来自成员国认捐的联合国会费。此前,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内设立的“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TechnicalCooperationamongDevelopingCountries,TCDC)特设局(Unit),是北方/发达国家同意与南方/发展中国家达成的妥协性安排。30年后,TCDC在年才得以升级为“南南合作特设局”(SpecialUnitforSouth-SouthCooperation),依然在UNDP的框架之下。 南南合作的复兴,如果我们还是以联合国体系内的协商结果为参照的话,是一个波澜不惊的过程。联合国大会在其年通过的58/号决议中将每年12月19日定为“南南合作日”。这个行为本身仅仅具有些许象征性意义,但这一举措为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多边机构将南南合作纳入其常规性工作方案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在联合国系统中,以推动“南南合作”为己任的机构,至少还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年以来在中国、巴西,埃及,印度,南非成立的南南工业合作中心(UNSSIC)。[1]在商品贸易领域,自年开始,在联合国框架下,每年一度的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得以举行。[2] 根据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内容之一,秘书长在年开始向大会提交《南南合作情况报告》(StateofSouth-SouthCooperation),以归纳和分析全世界的南南合作项目发展,并提出加强合作的建议。在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的《南南合作情况报告》文件列举了/17年度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的南南合作具体措施。其中第5条(全文共条)记载道:[3]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已有多个国家表示兴趣加入这一伙伴关系。该倡议侧重于加强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和设备连通、贸易畅通、金融一体化和民间交往。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联合国发展机构的文献中得到认可,这为倡议的推广和落实创造了有利的背景性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所倡导的南南合作项目进入了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那么,对中国而言,回顾南南合作运动的起伏,有助于思考如何稳步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发展事业。 本文粗略回顾南南合作运动的演变轨迹。年4月的万隆会议无疑是南南合作运动的标志性起点,到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设立“南南合作日”决议,大约50年间,南南合作运动从风起云涌走向偃旗息鼓。在21世纪的头十年,以“南南合作”命名以及具有南南合作性质的多边外交活动和机制重新获得重视。这两轮运动,都是以发展为诉求,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对推进“一带一路”事业有哪些启示?这是本文所设计要回答的问题。 有必要说明的是,围绕“南南合作”的记事,不仅信息量浩繁之至,而且自然地受到观察/分析视角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框架影响。因此,任何试图在章节篇幅内的讨论,都难免在视角上受作者个人偏好的左右,内容上具有选择性。作者在本文中的叙事和观察,基本目的是邀请读者一起思考中国与认可“一带一路”愿景的国家/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南南合作”的维度。 南南合作运动的兴起:—年 作为集体政治外交行动的南南合作运动,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有相当丰富的记载。[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因为它第一次把两大洲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在一起,并通过了措辞清晰的联合声明,而被广泛认为是南南合作运动的起点。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殖民地制度瓦解过程,一些原殖民地国发现它们虽然获得了主权概念下的政治独立,但是所面对的国际经济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认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并没有获得实质意义上的独立。他们要求得到原殖民地宗主国以及更广泛程度上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呼吁在跨国贸易和投资条件上得到革命性的改变,至少是要减少负面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外部阻力。通过群体会议而展现政治团结,从而增加与前殖民地宗主国以及更广泛的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是南南合作运动兴起的重要动机。 在万隆开启的发展中国家展现团结力量的运动,于年9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来自25个国家)会议上得以延续。除了表明在政治上不加盟美国或苏联分别牵头建立的军事/外交集团之外,不结盟运动的核心诉求包括维护经济权益,消除经济不平衡,废除国际贸易中心的不等价交换,发展本国经济。[5]贝尔格莱德会议延续并拓展了万隆会议的诉求,维系了原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外交中的集体谈判势头。 作为一个集体谈判的国际政治运作机制,不结盟运动因为不设总部,无常设机构,无成文议事章程而难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决策机制。另外,为了体现“非殖民化”和运动参与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结盟运动各种会议均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成员间所达成的声明或领袖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会后对成员没有约束力。就将自己区别于老牌帝国主义以及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集团政治的运作模式而言,不结盟运动成功地展示了它的特性。但是,在类似联合国这种多边外交平台上,它无力成为一个集体谈判的机制。 南南合作/不结盟运动的发展诉求,就联合国多边政策协调机制建设而言,于年获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年,为期3个月(3月23日—6月16日)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UNCTAD)在日内瓦召开。根据首次会议所达成的决定,联合国将定期举办贸易与发展会议(每四年)及其理事会(一年一次会议),并为这两次会议提供秘书处服务。[6]展示发展中国家集团谈判策略的“七十七国集团”也同期产生。该集团(如今已扩大到个成员)是冷战期间南南合作运动的经济社会议题主力,与不结盟运动的政治诉求相呼应。UNCTAD的成立标志着南北之间开始就发展问题展开结构性、制度性对话,也标志着南北方之间的集团协商机制(“北南对话”[7])正式形成。 在战后国际经济外交史上,以立章建制作为参照点,年是南南合作运动的高潮。这一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文件。同年12月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宣言》的概念性框架在年10月于开罗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首脑会议提出,《宪章》则是由77国集团在的《利马宣言》中提出。这两份文件的提出,由于在文字上确认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主权,承诺改革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制度和贸易条件等,标志着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为核心诉求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 这20年间,南南合作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不止研究文献中经常性被提及的纲领性文件。例如,在77国集团牵头推动通过的《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年)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年),尽管各款公约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有所不同,每一款都吸收了海运、航空等各项单式运输公约至此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国际运输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对跨国货物和人员运输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幅度增长,为全球经济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发挥了有益的作用。[9]此外,在UNCTAD平台上,由不发达国家集体提出动议的综合商品方案[10]、普遍优惠制[11]等,对战后初级产品的跨国贸易方式的创新,都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推动被统称为南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北方或工业化发达国家的集体努力方向。对于北方国家而言,如何构建与原殖民地经济体之间——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方面——的贸易关系,也有必要依赖多边外交机制。年,联合国发展署(UNDP)成立。这是一个在联合国既有机构基础上的重新组合,其负责人官阶处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之后的第三位,有常规性职员编制和预算保障的机构。成立发展署的动议,来自发达(北方)国家,尽管过程中北欧国家的热情遭遇了美国的抵制,但是,因为每一个联合国成员都有让UNDP设立办事处的义务,其影响力的广度是不可忽视的。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日常性往来而言,UNDP的国别办公室发挥了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机构与驻在国政府不同机构沟通的功能。甚至可以说,UNDP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板块在项目落实环节的代表处。[12]在联合国机构体系中,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另一个机制是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nomicandSocialCouncil,经社理事会)。理事会于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负责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后续活动,通过旗下的五个地区分会发挥信息搜集和政策沟通的作用。发展署与经社理事会相互支撑,成为联合国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常驻机构。 如前文所提及,年UNDP设立了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CDC)功能。这个发展,可以说是一个由发达国家集体主导的机制吸纳了一个由发展中国家集体推出的动议。此后,具体方案的推进,取决于单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意愿和能力。就像如今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官方网页中的自我简介所暗示,TCBC的设立,可以说是南南合作运动在20世纪的联合国官僚体系内建章立制所取得的最后成就。 万隆会议之后的20年间,南南合作运动在多边外交中的声势得以维持。但是,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格局。南北差距和一些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新秩序”,沦为一些南方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的口头禅而已。原殖民地国家/第三世界之间的政治团结,并不容易维持。 南南合作运动的式微:—年 年4月,一场题为“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及合作”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近三十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名政治家、学者出席。这次会议的中文版论文集,标题是“南南合作勃兴”。[13]其实,中文措辞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作为国际政治运动的南南合作浪潮式微的认知。正如年创刊,政治立场上同情、支持南南合作/不结盟运动的英文《第三世界季刊》(ThirdWorldQuarterly)中对北京会议的综述所言,“南—南,甚至南—北主题的会议,已经成为同一批人围绕同样的话题重复同样观点的例行公事。这些会议所产生的宣言和声明也大多似曾相识,了无新意。”[14]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年的“石油危机”——因不满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作为,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采取集体行动,针对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石油禁运——就不会有北方国家在“北南对话”(North-SouthDialogue)框架下聆听南方国家的诉求。南、北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就自身利益驱动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这种根本立场的对立,经过冗长的多边谈判的磨炼,造就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等“装点门面的协议”。围绕穷国的外债负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跨国公司的行为规范等等议题,双方的分歧不仅是程度上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层面的南辕北辙。[15] 更为致命的是,在南南合作阵营内部,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所必需的原材料。当某项大宗商品被用做政治外交的武器时,占出口市场比例高的政府能够获得某种谈判优势。而依靠大宗商品进口来发展经济的南方国家,则在动荡的初级产品贸易中受损。这种损失,并不局限在原材料贸易环节:因原材料的供应缺乏稳定性和价格突变而导致的加工环节不稳定,影响更为广泛、长远。所以,尽管不少南方国家的出口支柱性产品是大宗商品,在南南合作或不结盟运动的框架下,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也是显然易见的。 年10月,由发展中和发达国家首脑共同参加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来自五大洲的14位发展中国家和8位发达国家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正式地专门讨论南北关系问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也是冷战期间类似话题、类似规模的最后一次会议。美国总统出席了坎昆会议。会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发生了质的改变:从倾听、容忍、有所适应转向对立,开始公开地攻击、抵制南方国家和它的集体目标,瓦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团结。[16]全球化将发达国家的政治理念、政治与经济体制设计、社会组织逻辑、商业法规和惯例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取代“北南横沟”(North-SouthDivide),而成为国际间有关发展(development)的总括性研究议程。 其次,正如退休前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yatea.com/xytbz/11092.html
- 上一篇文章: 谁才是踏板小钢炮本田ADV150vs雅马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